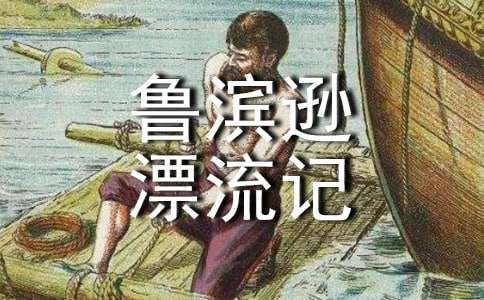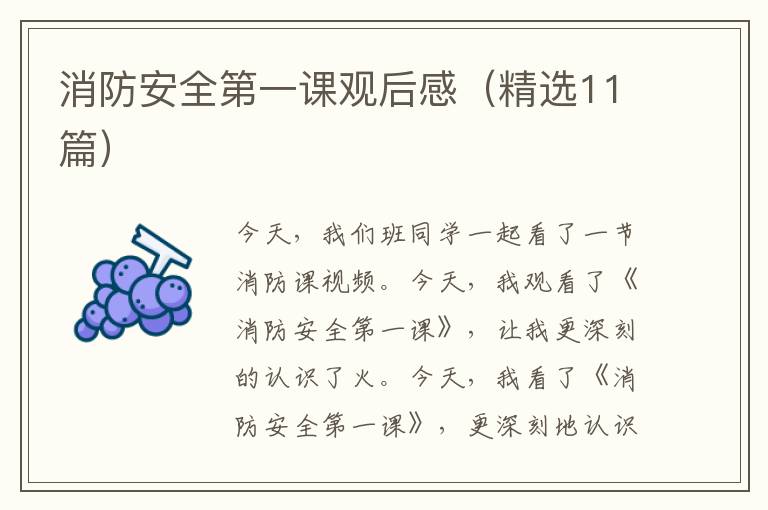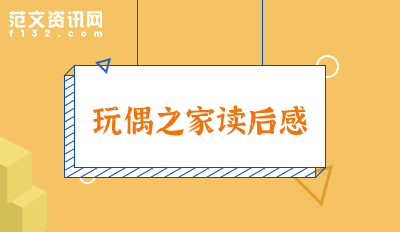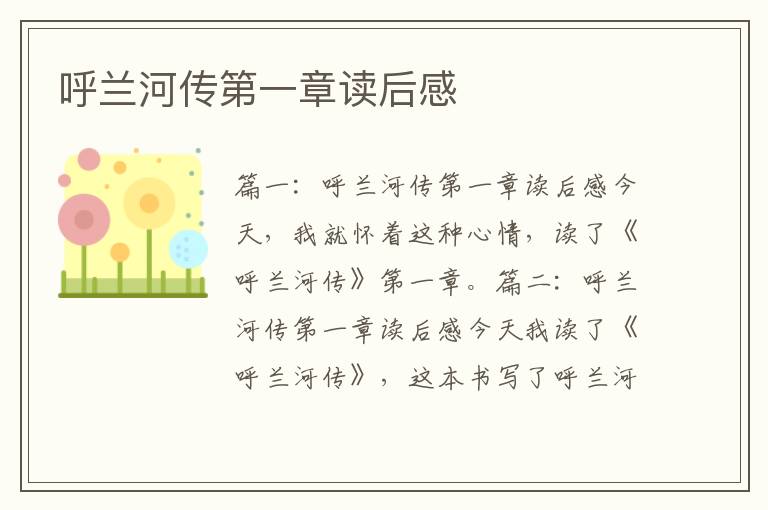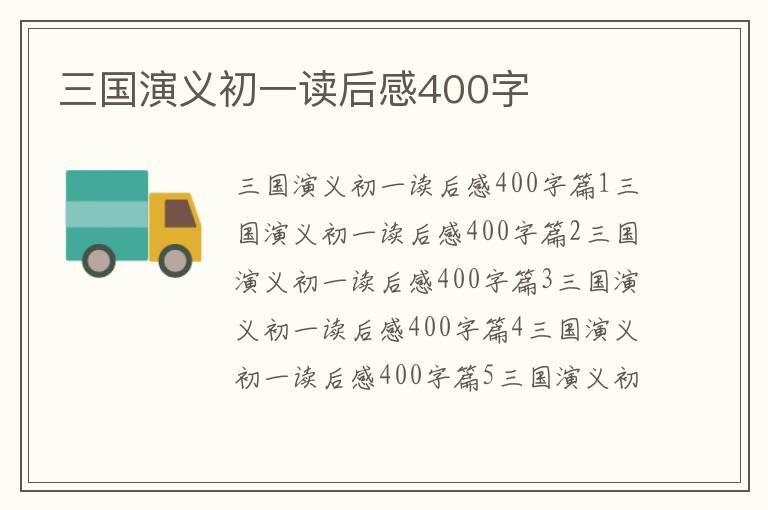某位同學讀《論語集注》后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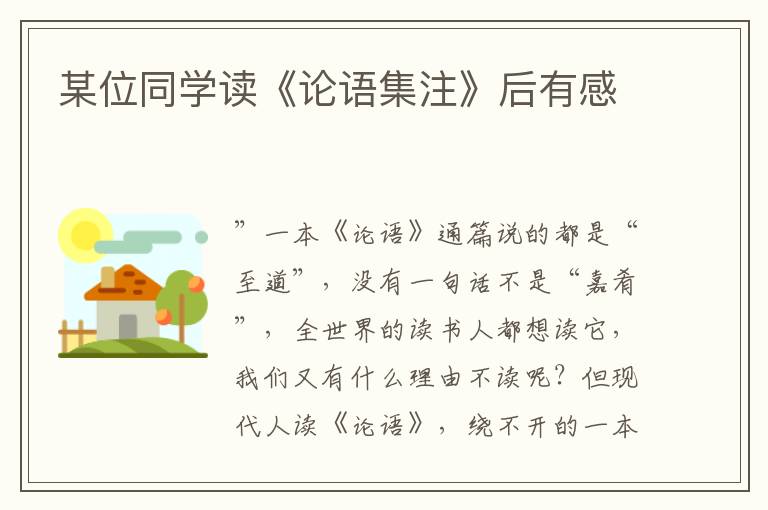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一本《論語》通篇說的都是“至道”,沒有一句話不是“嘉肴”,全世界的讀書人都想讀它,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讀呢?但現代人讀《論語》,繞不開的一本注,就是朱熹的《論語集注》。
朱熹何人?在沒有閱讀他的書之前,殘存在我腦海中的只有那句“存天理滅人欲”,和那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這本書對于我是有一定難度的,但既然決定要讀了,就得硬著頭皮看下去,不懂處查資料,還是不懂就多看幾遍,直至于弄明白。“時復思繹”,雖未到“浹洽于中”的程度,一本書讀完內心多少有所觸動。因為閱讀量的狹窄,這種體會具體還做不到一個貼切的表達,只能大體說說一些零散的感受,暫先寫一篇讀后感,以此作為紀念。
一開始看書,必然陷于章句之間,而忘記總覽全篇,或全章,在個別字詞之間糾纏;或有時,看了下一句又忘了該與上一句如何去關聯;有時又拿不準這句話是引用了說話人自己的闡發,還是來自于哪一本書的典故可以參考。。。于是讀讀、停停、查查。雖然過程很慢,但不這么讀書,也就無法很好的理解文本,讀書“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但文義只是第一關,“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又“須要識得圣賢氣象”。就如你看一個人,你不能只關注他的眼睛、鼻子這些具體器官是怎樣的一個形狀,你看到的最終得是一個形體與內外氣質相結合的人,只有這樣才算認識了這樣一個人。所以,對于讀《論語》,也只有這樣去讀才算真正讀懂了這本書。
說到“圣賢氣象”,它像是一種抽象而高遠的存在,如顏淵感嘆孔子之“道”的“無窮盡、無方位”時所說的那樣“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看起來,這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高度。然而,通往圣賢的道路又是有序可循的,孔子說“參也魯”,圣門學者,才氣過人的人眾多,最終是質魯的曾子得到了圣道真傳,成為僅次于顏淵的一代宗圣,所以圣賢之為學貴在一個誠字。
學者若如無心去體會這種“圣賢氣象”,不著力于“熟讀玩味。。。將圣人言語切己”,那么讀一本《論語集注》也許就如拿一本《漢語字典》認字一樣沒什么區別,那么在求學的路上也就永遠不會有機會到達學問的“高明之域”、“精微之奧”,永遠入不了室。
什么是“圣賢氣象”?“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孔子是圣人,顏回近似圣,而孟子則當如賢人。宋理學家程顥通過對儒家這三位先哲言行舉止的形象比喻,將三人由于內在精神修養的不同而呈現出來的外在的人格形象的不同闡釋出來,為我們學習模仿古人的圣賢氣象提供了一個參考方向。
看《論語》中,“顏淵、季路侍”這一段,對于圣賢之志的描述:
子路曰:“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愿無伐善,無施勞。”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三者之志“皆與物共者”但有“小大之差爾”。子路之志“亞于浴沂者也”,顏子之志“未免出于有意”,而孔子之志“如天地之化工”,觀其志,圣、賢之氣象如天地分明。
人之為學,具體該如何做,才能踏入“圣賢之域”?
孔子給出的回答是:“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為學先立志,如何立志?“志于道”。如何存志?“據于德”。如何用德?“依于仁”。而“游于藝”,則使人從全方位得到涵養,從事物的本末到自身內外的修養以及日常應用,無一遺漏,最終融會貫通,進入“圣賢之域”。
從為學的目的上看,圣賢之論學為“為己”。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一個人為學若“為己”,能從內在的驅動力出發,發自內心的提升自己,尋求內在道德修養的超越,最終定然成就一番利己、利人、利社會的崇高事業;為學若“為人”,將學問作為一種門面的裝飾、名利的工具,最終必然迷失自我。這是為學最忌諱的,“放于利而行,多怨”。
圣賢無不愛,但亦有好惡之心。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無論是圣人孔子,還是學生子貢,都有愛憎分明之心,只有愛憎分明,方能分清“無可無不可”之界限,否則豈不成了“鄉原”?鄉原,“似德非德”,實為“德之賊”也,使人辯不清是非,極容易因毫厘之差而“失其中正”,故為君子所“深惡之”。
以上是對于圣賢之立志、為學、好惡等方面的粗淺感受。
在《論語》通篇中,很難見到孔子滔滔不絕的時候,相反,他曾說“予欲無言”,只有極其難得的一次,他跟子路發誓說,“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對于學生,他遵循的是“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對于資質尚淺,無法領會圣學的學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對于不同的學生,問同一個問題,他的回答也有所不同,他會采取針對性的方式,給予糾偏,始終遵循中庸之道。但,孔子也會退而求其次,對于學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但中人難得。
圣人氣象,體現在教學中,日常互動中,與各類人對答中,無處不在,無法一一列舉,《論語》整本書沒有一處不好的。
在最終篇的最后一條注中,朱子引用尹焞的話作為結尾,“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于侮圣言者乎”由此激勵后學,表達對后學的殷切期盼之心!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圣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于《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也就是說,哪怕過去幾千載,只要用心閱讀,我們依然可以從書中,學習到古圣賢的深切叮嚀與諄諄教誨,從而感動于他們透過時間長河輻射而來的“圣賢氣象”。